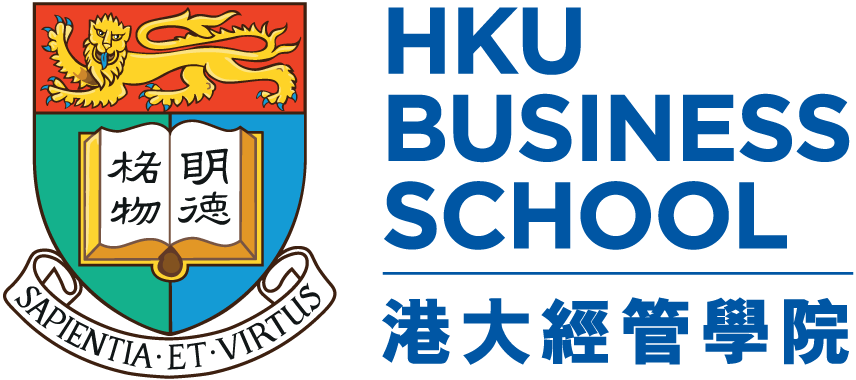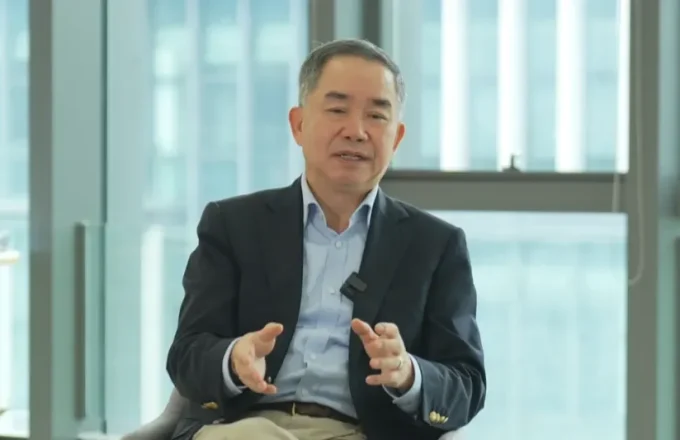The U.S. Debt Storm and the Reshuffling of Global Finance
2025年4月,全球金融市場見證了一場教科書級的信用危機。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短短一周內飆升逾50個基點,觸及4.5%的高位,創下自2001年九一一事件以來最大單周漲幅。這一現象徹底顛覆了美債是全球最安全資產的傳統觀點,也暴露了美元信用體系的深層裂痕。
要理解這場危機的嚴重性,需從「無風險利率」這一金融學基石概念入手。 美國國債長期被視為全球資產定價的錨點,其收益率用以計算股票估值、外匯定價甚至住宅按揭利率。這種信用的核心在於美國政府的償債能力——理論上可通過印鈔償還債務,因此「不可能違約」。然而,當市場開始質疑這一邏輯,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便面臨挑戰。
危機的導火線看似是技術性因素。4月8日,美國財政部拍賣3年期國債時需求慘淡,競拍倍數僅2.26,創2023年以來新低;但更深層的結構性矛盾,在於對沖基金的基差交易(basis trade)放大了市場波動。這種策略通過50倍槓桿押注長短期國債價差,若收益率波動超過1%,超過6000億美元的頭寸被迫平倉,就會引發連鎖踩踏。與此同時,傳統美債買家集體撤離,其中中國連續兩個月減持美債,並增持黃金;日本因日元危機拋售美債自救;沙特則通過香港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簡稱CIPS),以人民幣結算石油交易。
這3件大事的疊加並非偶然。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美債持有國不斷減持,削弱美元的官方儲備需求;日本被動拋售,暴露美債在極端匯率波動中的脆弱性; 沙特嘗試本幣結算,則直接挑戰美元在大宗商品定價中的壟斷地位。當支撐美元信用的「官方儲備錨」、「匯率穩定錨」和「大宗商品錨」同時鬆動,市場終於意識到,所謂無風險資產的神話,本質是全球化時代各國對美國財政與軍事霸權的集體妥協。
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2025年聯邦政府利息支出或達1.5萬億美元,佔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若美債收益率持續攀升,美國可能陷入借新還舊的債務深淵,並且觸發主權信用危機。這一邏輯的崩塌,標誌着二戰後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金融秩序,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傳統金融模型中,股市暴跌通常會推動資金湧入國債避險,但本月的市場表現徹底擊破這一規律。短短一星期,美股已蒸發8萬億美元市值,美元指數跌破100關口,美債卻未獲避險資金青睞,反而出現股債匯「三殺」。反常現象源於白宮政策的搖擺與地緣政治博弈的交織。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成為市場動蕩的催化劑。在8天內,其團隊3次調整對華關稅稅率,一度高達145%。政策不確定性導致企業無法制定長期生產計劃,甚至90天內的供應鏈安排都產生混亂。投資者因此墮進「流動性黑洞」,無論股票、債券還是外匯,所有資產都變成高風險標的,唯一選擇是持有現金。即便白宮緊急暫停部分關稅,但保留的10%基準稅率與90天緩衝期仍未足以緩解恐慌。
尤其深遠的影響來自美元霸權的自我削弱。美國頻繁將金融系統武器化,迫使中國、俄羅斯轉向本幣結算,兩國83%的能源貿易已脫離美元體系。沙特更通過香港的金融基礎設施,以人民幣結算石油交易,直接挑戰美元在大宗商品定價中的壟斷地位。市場難免擔憂,美國可能通過合法違約手段(例如強制將短期國債轉換為50年期零息債券),以化解債務危機。換言之,美債將從避險工具淪為風險源頭。
這場危機不僅改變了市場運行邏輯,更重塑了人們對金融體系本質的認知。 以下三大宏觀經濟指標的變化,有助普羅大眾掌握新秩序的關鍵。
美債收益率曲線倒掛深度。收益率曲線倒掛(短期國債收益率高於長期)是經濟衰退的警號。目前10年期與2年期美債利差擴大至-120個基點,創下1981年以來最深倒掛。由此可見,市場對美國長期財政的可持續性生疑。當政府債務利息支出吞噬三分之一財政收入(2025年或達1.5萬億美元),投資者自然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
全球外匯儲備中美元佔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例已從2001年的73%降至2025年首季的52%,降幅與人民幣、黃金儲備上升同步發生,反映各國央行對美元信用正重新評估。沙特通過香港的CIPS系統,以人民幣結算石油交易,正是去美元化進程的縮影。
人民幣跨境支付比例。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使用率從2022年的2.7%躍升至2025年4月的9.3%。香港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中心,其人民幣存款規模突破1.2萬億元,成為觀測地緣經濟權力轉移的重要視窗。
2025年的金融風暴,本質是對「美國例外論」的集體反思。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關稅與制裁來維持霸權之際,市場卻還以拋售美債、美股、美元的「三殺」。這場危機揭示了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世界金融體系正從單一美元錨點轉向多極化格局。
香港的角色,恰如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鈎時的轉口港,既是舊秩序的見證者,也是新規則的試驗場。其聯繫匯率制度的動態平衡、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以及作為東西方資本橋樑的功能,都在為個人提供檢視宏觀經濟變局的微觀視角。
當紐約的投資銀行交易員還在爭論美國聯邦儲備局何時降息,香港的銀行家已經悄悄做多越南盾和馬來西亞令吉;這些貨幣背後是正在承接中國產業鏈的東南亞工廠。這大概就是全球化的嶄新發展:美元霸權漸露疲態,靈活的小型開放經濟體則率先找到生存縫隙。香港正在這條裂縫中積極地播種未來。
章逸飛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高級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