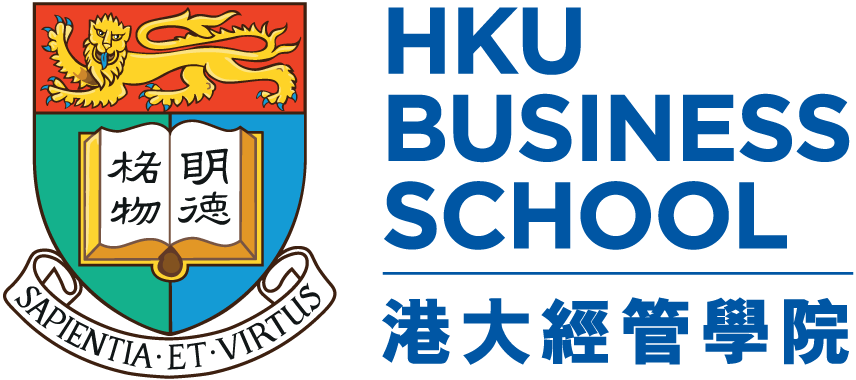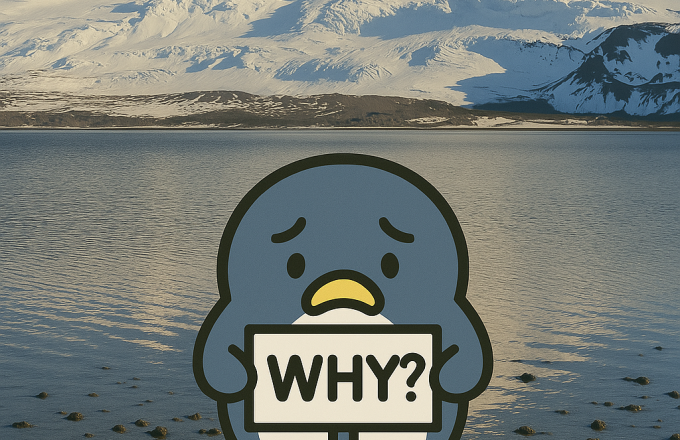全球化逆转下的雁行模式2.0
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在1930年代提出的“雁行理论”(Flying Geese Paradigm),描述东亚国家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发展。雁行理论指出,作为“领头雁”的日本率先完成工业化,并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带动其他国家发展,令东亚经济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梯度推进的产业分工体系,其结构有如天空中的雁群。此理论在二战后几十年的经济实践中得到验证,日本企业全球扩张的策略不但塑造了东亚制造业的格局,也成为后来中国、南韩等国家企业全球化之范本。
放眼今日的世界,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产业政策和政府干预的重要性,激烈的竞争带来国家在商业和技术上的互相防备,这个重要的理论看似已经不再符合现时经济局势。当前世界经济再次面临变革关口,自动化、人工智能、地缘政治冲突和供应链重组正在重塑全球制造业的版图;曾经主导产业转移的“雁行理论”是否仍然适用, 对我们了解今日中国经济转型,及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互动,又有甚么参考作用?
1985 年,面对美元利率上扬及持续升值,美国召集当时的五国集团(美、日、英、法、西德)在纽约广场饭店签订影响深远的《广场协议》,通过对外汇市场的联合干预,引导美元对主要货币有序贬值。日本所受影响最大,两年间日元升值超过1倍,令日本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下降,严重打击该国出口,尤其是汽车与电子产品等行业。
面对汇率冲击和国内成本上升,日本企业随之展开史无前例的海外生产转移浪潮,汽车、电子、家电等行业的龙头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迁往亚洲各地,尤其是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即后来的亚洲四小龙。此举不仅是为了规避汇率波动,更是基于雁行理论的逻辑:日本企业在本国完成产业升级后,将低附加值制造环节搬到成本较低的地区,而这些后发经济体在承接日本产业的过程中,也逐步实现自身工业化。到1990年代初,随着四小龙经济水平提升,日本制造业进一步向东南亚扩展。地理位置临近,且有政策支持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成为新的目的地。
以丰田在北美市场的策略为例,通过建立生产基地和进行本土研发的方式融入美国的产业链。1980年代在美国首先推出的Camry房车,不但在北美市场广受欢迎,也成为丰田打开国际市场的一款旗舰型号。2000年代初,丰田超越福特,并在2008年超越通用汽车(GM),成为全球销量第一的汽车制造商,可见注重品牌建设策略所带来的高回报。
日本企业虽然通过全球化获得新的发展机会,但日本经济却为这一轮全球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大量企业将生产线外移,该国制造业逐步“空心化”(hollowing out)。就业机会减少,制造业投资停滞,生产总值增长陷入长期低迷,日本经济进入“迷失的十年”。日本企业因而开始反思成本驱动型全球化策略的可持续性。踏入21世纪,日本企业的全球化策略随着世界经济格局改变而发生变化,尤其关注品牌的塑造,并与聚焦技术获取(technology acquisition),表现为大规模的海外并购和研发投入。
近年来,对外面对美国持续打压,对内面对市场增速放缓,中国内地企业也一如40年前的日本企业,处于必须求变的关键时刻。然而今天的环球经济与1980年代相比已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雁行理论是否依然适用?内地企业又是否能与上次一样成为领头雁,为亚洲带来另一次突破的机会呢?
值得留意是,1980年代的雁行模式源于非常独特的历史时期。首先,此理论所描述的“梯度推进”结构有赖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大盛时的国际合作,不但讲求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互信合作,更要放下竞争和敌意。在逆全球化声势日益凌厉的今天,贸易保护主义和不稳定的地缘政治会令产业和技术的转移举步维艰。
2010年代以后,曾为“领头雁”的日本亦因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而开始对全球化策略进行结构性调整,各大企业甚至出现产业链回归及再本土化的趋势。2022年,索尼就宣布将与台积电合作,在九州兴建芯片工厂。本应将资源投入下一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纷纷推动产业链回归或近岸外包(near-shoring),以管理产业链的抗风险性。正在苦等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则眼见经济发展机会愈来愈少。
科技进步及自动化生产的大规模应用也是雁行理论受质疑的另一原因。自动化生产可令劳动密集型商品的成本大幅降低,切断维持雁行机制运转的主因:若机械人可以替代廉价劳动力,企业就不再需要将生产链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地区。世界银行一项研究发现,国家的工业机械人数量超过某一临界值后,其数目与该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就成负相关关系。换言之,自动化生产愈发达的国家, 在其他国家投资进行产业转移的动力就愈低。
中国内地企业“出海”重新演绎“雁行模式”
中美竞争虽为国际贸易平添重重障碍,但也为多年未见变化的环球经济格局注入了新的活力。美国政府透过各种政策控制中国经济崛起,导致企业纷纷开始采用所谓“中国+1”的策略,在保全中国市场和生产基地的同时也寻求位于中国周边第三方国家的供应商,以分散地缘政治风险,愈来愈多中小型经济体因而得以参与全球供应链。其中以越南、泰国、印尼等东盟国家,以及墨西哥、巴西等部分中南美国家获益最多。以东盟国家为例,2023年中国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总额超过250亿美元,按年增长34.7%。长期被几大贸易国主导的供应链变得多元化,有助于建立多元的国际规则及体制。
中国内地企业“出海”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崭新商业模式。哈佛商学院教授乔许·勒纳(Josh Lerner)等人在最新研究中发现【注1】,中国企业在近20年来壮大的同时,其商业模式也渐对新兴市场带来正面影响。中国的风险投资者在全球投资中担当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在新兴市场的投资也大幅增加。又因为这些投资通常倾向于进入由中国企业主导的行业,包括教育科技、数码科技及金融科技等,导致这些行业在全球新兴市场当中的发展明显快于其他行业。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企业主导的行业中,新兴市场的本土投资者也开始借用中国企业投资和商业模式来进行投资,加大创业创新力度,勒纳的研究总结中国对外投资,对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对比日本企业外移时期向周边国家进行企业转移,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在全球化过程中,对新兴市场带来资金和商业模式改变,未尝不是对雁行理论的全新诠释。尽管时代不断变化,但国际合作既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元素,未来的环球经济亦势将朝着更多元化和科技主导的方向迈进,不同规模的国家,不同行业的企业都会有更多机会参与全球供应链。
不过多元化并非自然发生,而需要不同国家通力合作。近期特朗普新政府对贸易伙伴甚至盟友的重关税政策,有机会会引起覆盖全球的贸易战。一旦环球经济陷入贸易战,多边贸易成本变得更高。各国为了保障自身利益,或会选择缩减海外投资和合作。长此以往,只会动摇各国对合作的信心,令中低收入国家的发展难上加难。
注1: Lerner, Josh, Junxi Liu, Jacob Moscona, David Y. Yang (2024) “Appropriate Entrepreneurship?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Hava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对外事务)、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亚洲环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亚洲环球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