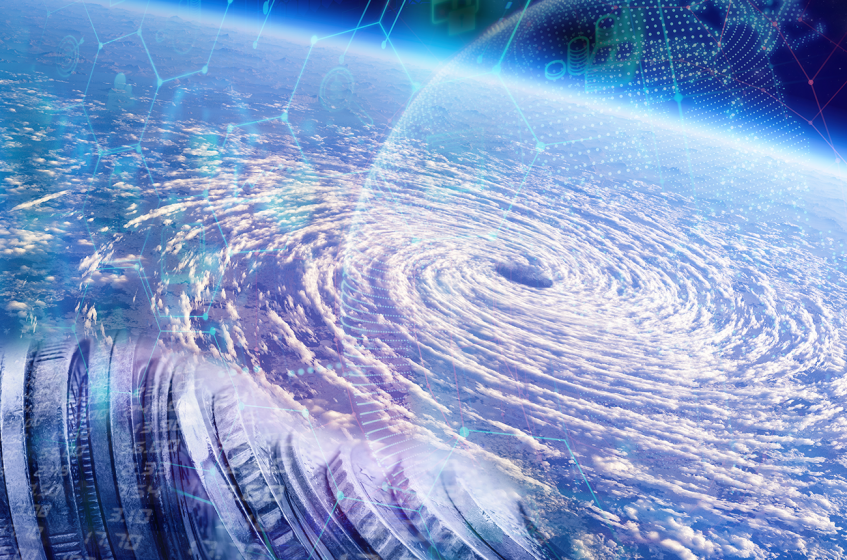
气候变化与央行政策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William Nordhaus在领奖致词时说,技术革新带人类走出石器时代,但气候变化却以最严峻的方式,威胁将人类打回原形。气候变化的危机、对策及国家之间的互动,将会是本世纪的主要议题之一。上周日开始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 会议,可能是有关讨论的一个里程碑。
COP26即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下的第26届缔约国大会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该会议自1995年开始每年举行。2015年的第21届会议,达成了著名的巴黎协议。各国的共识是让全球气温升幅,与十九世纪工业化之前比较,最多上升摄氏2度,并尽力争取只上升1.5度。各国同意大幅度减少碳排放,并定下「国家自定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NDC),即本国的减排承诺。按当时各国的NDC总额计算,坊间普遍认为各国的NDC 目标不足以达标,但各国会每5年检讨和评估,并向上修订NCD。原定去年召开的COP26,因新冠肺炎延迟到今年。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检讨6年来全球减排的状况和各国修订后的NDC、以及下一步的政策。
要达到上述的1.5度升幅,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大幅减少。按国际能源署的资料,去年全球和能源有关的碳排放减少了5.8%,但这只是因为新冠肺炎导致经济活动收缩,估计今年会回升。现时与工业化前相比,全球气温已上升了1.1度。
在COP26开幕前,G20峰会刚好在意大利罗马召开,议程也包括气候变化。峰会的20个成员国,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80%,本应更有责任地提出应付的方案及承诺,促进COP26的讨论。然而,G20峰会的结论乏善足陈,不是原地踏步就是模棱两可。COP26约200个国家地区的与会者,要在这约两星期中达成协议,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将会困难重重。
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在经济层面较为明显。单看这些年来,世界各地因极端天气导致的人命和财产损失,便不言而喻。这些损失也构成一定的金融风险。此外,气候变化亦无声无息地影响着地缘政治的格局。例如电动车市场的发展,增加了电池中某些金属的需求,出产这些金属的国家便奇货可居。相反,多年来依靠出口化石燃料的国家,如沙地阿拉伯及俄罗斯,前景便需重新规划。地球暖化下水平线上升,会迫使低洼及沿海地区的居民大规模迁徙,造成国际移民潮。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一些海军基地也需要另觅容身之所,或会影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本来冰封的北极洋会因为溶雪而慢慢地腾出一些航道,这或会增加国际贸易的船运路线,也自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典型的负面外部效应,最直接有效的应对方案是通过税收将排放的社会成本内化,并建立碳排放许可证市场,让对排放有不同成本和需求的生产单位互相交易。此外,政府也可以补贴有关减排和开发新能源的科研项目。这些都可算入财政政策的范畴。大约在五、六年前开始,货币政策也被列为应付气候变化的一项工具。
英伦银行的前行长卡尼(Mark Carney)大概是最早倡议央行政策要针对气候变化的其中一人,他在2015年发表有关演讲后,引来一些批评,指那是央行的「使命偏离」(mission creep)。其后,他得到好些同行的支持,包括现任欧央行行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及联储局理事会成员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后者被认为是可以威胁鲍威尔连任联储局主席的人选。
央行帮助解决气候变化的看法,很快在全球各地被广泛接受。在2017年底,有8家中央银行成立了央行绿色金融网络 (Network of Central Banks and Supervisors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NGFS)。顾名思义,那是央行主动绿化金融的举动。这个组织的央行成员,至上月底已增加至98家,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管局。
央行针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可以监察金融机构的有关风险,也可以诱导金融机构贷款给某些绿色行业。前者的争论较少,后者则大有商榷余地。
央行的传统功能,是稳定物价和提高就业,特别是前者。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后,金融稳定成为了全球央行主要的政策目的之一,央行也就多了执行宏观审慎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y)的职能。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和不确定性,增加了各个不同领域的金融风险,央行在这方面自然责无旁贷。
至于将货币政策向绿色行业倾斜,以减少碳排放,这差不多就等同是产业政策。从外部效应的角度来看,要提高绿色行业的生产效率,便要增加高污染产业的生产成本,并减少绿色产业的生产成本。用央行的政策工具来说,便是减少贷款给高污染产业、多贷款给绿色产业。但同样的结果,可以通过政府对前者征税、对后者补贴达致,为何不交由财政部处理?央行的相对优势在哪?
或许会有这样的想法,目前联储局和欧央行仍在进行量化宽松。既然要大量买债,那就不妨多买绿色债券,有人称之为绿色QE。又或者在旧债期满时,以取回的资金买绿色债券,这样一来可保持基础货币不变,不影响原有的货币政策;二来又可以辅助绿色产业。不过,若这里说的是二手市场的债券,不影响有关企业的利息成本。央行作怎样的买卖都无补于事。反而财政部的税收补贴,还是行之有效。
但更根本的问题,是央行的使命是什么?在公共经济政策中,政府可以做的包括生产资源的分配、生产成果的再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央行的功能一直都是后者,若要同时对不同行业或企业作贷款或利息的取舍,便混淆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一来使央行的运作变得更加政治化,二来亦减少了央行的独立性,这些都不利央行的传统货币政策功能,削弱宏观调控的效果。政策的目的多样化了,但政策的效果也模糊了。还有,不同的政策之间可能有矛盾,如央行政策向绿色项目倾斜,但那些项目创造的工作岗位较其他项目为少,那便和央行的提高就业使命有所冲突。这会影响社会对央行维持政策目标的信心。
经历了全球金融海啸和新冠肺炎后,央行被赋予的职能愈来愈多,货币政策俨然成为经济的万应灵丹。除了气候变化外,另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主要议题是贫富悬殊。也许过不了多久,央行也要负担起收入分配及其他政治社会议题的责任。但无论是作绿色产业和污染产业之间的分配、或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货币政策都显得尾大不掉,并非合适的工具。
陆炎辉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