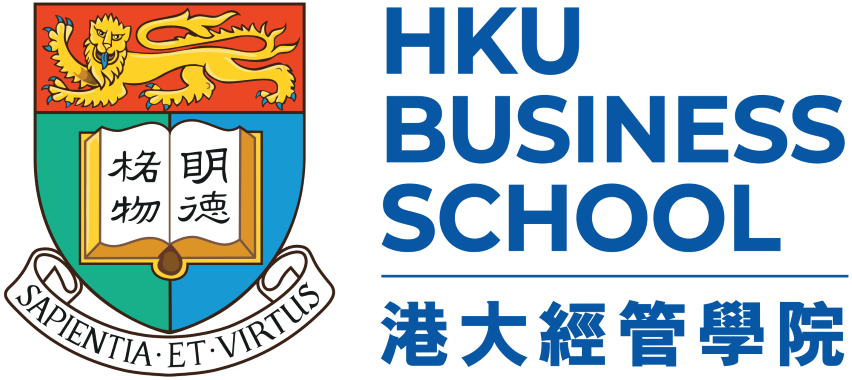債務重重的全球經濟
一星期前,人大常委會批准了國務院增發一萬億元人民幣的特別國債,所得款項於今年及明年全部轉移給地方政府,作為各地在自然災害後的重建及防災工程之用。有關措施雖然針對自然災害,也會在當前經濟復甦時起到推進作用,體現出較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時也反映出地方政府的捉襟見肘,需要中央政府的幫助。雖然一萬億元是個龐大數目,但中國的國債規模不大,約為GDP的20%,應不會造成很大的負擔。至於人民銀行會否放寬流動性幫忙融資,須待觀察,畢竟也要考慮人民幣匯率的弱勢。
政府以發債融資來帶動經濟活動,是司空見慣的例行公事。但債務是把雙刃劍,適當的發債規模和所得資金的有效運用,可以帶來更多更早的生產和消費,而錯誤的資金投放,特別在過度發債的情況下,不單浪費資源,亦會成為將來的負累。環顧全球經濟,無論是債務總額或作為GDP的比例,在過去十多二十年都有迅速上升的趨勢,在全球經濟發展的前景中投下一個陰影。
根據聯合國的資料【註1】,全球各政府發行的、包括對內和對外的公債,在2022年達到92萬億美元,是2000年17萬億美元的5倍多,而2022年的全球GDP只是2000年的3倍,即公債對GDP的比例上升了三分之二。92萬億美元公債中,由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行的比例分別為70%和30%。眾所周知,美國發行的公債最多,佔全球公債的34%,對全球的影響亦最為直接和深遠。
憑着美元的國際地位,美國政府可以恣意地欠債纍纍,到今年中已超過32萬億美元,為GDP的120%。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今年6月發表的報告,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會由2023年佔GDP的5.8%持續增加至2053年佔GDP的10%,增加4.2個百分點。有趣的是,增加的百分點差不多全部來自利息支出。美國聯邦政府今年支付的利息是GDP的2.5%,估計到2053年是當時GDP的6.7%,也是增加4.2個百分點。換句話說, 美國政府要發愈來愈多的新債來應付愈來愈多的利息支出。國債排擠了私營部門的活動,但卻並非用在有建設性的項目上,對經濟自然是弊多利少。同時,美國政府的發債會帶動全球利率上升,導致其他地區的經濟及債務困難。
除了美國外,好些已開發國家的公債佔GDP比例也很高。最明顯的是日本,約為260%,但日本的儲蓄率遠高於美國,而日本的金融市場相當內向,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應不會很大。此外,歐洲的希臘、意大利、法國和英國都有相當規模的公債。在目前俄烏戰爭和中東危機的影響下,歐洲經濟面對多方面的困難,過重的債務自然是個想扔掉的包袱。
和已開發國家比較,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演變相對來說更值得關注。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增加,不難理解。她們的政府基於低生產水平的稅務收入,自然不足以應付即使最基本的民生及建設開支,更遑論應付新冠疫情和氣候變化的費用。在2011年,公債高於GDP 60%的發展中國家只有22個,到2022年已迅速增加至59個。此外,當前的國際金融架構亦造成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困難。
首先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低收入國家並不富裕,國內沒有足夠的資金,自然要向國外舉債。但在國際市場上舉債,債務自然以美元或歐羅等硬通貨計算,亦需要以同樣的貨幣償還,而出口是賺取硬通貨的主要來源。從2010至2021年,發展中國家政府向外國借款額由她們國家GDP的19%增加至29%,而出口所得的外匯用於償還外債的比例亦由3.9%增加至7.4%。若債務期間國內貨幣兌主要貨幣貶值,還款的負擔亦隨即上升。
發展中國家公債的另一個趨勢是,私營債權人(如商業銀行)的比例愈來愈高,由2010年的47%增加至2021年的62%。相反,多邊開發銀行(如世界銀行)所佔的比例則減小。私營債權人的貸款主要從商業角度出發,條件不如多邊開發銀行從促進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般優惠。此外,債權人的多樣性也增加了有需要時債務重組的複雜性,因而拖長了談判的時間和增加了欠債方的成本。簡單來說,若只有一個債權人,通過債務重組提高欠債方償還債務的能力,會全數有利於該債權人。但若有多個債權人,他們都不會那麼願意重組債務,因為欠債方的僅餘資金會先還給那些追討最積極的債權人。換句話說,私營債權人的多樣化導致的搭便車問題,妨礙了債務重組的談判。
另一個問題是發展中國家的借貸成本遠高於已開發國家。由於前者的違約風險較高,融資的成本也自然相應上升,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市場籌集的資金。若比較今年上半年不同地區的十年期政府債券收益率,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分別是11.6%、7.7%和6.5%,都大幅高於美國的3.1%和德國的1.5%。然而,這些收益率差別那麼大,能否全由違約風險解釋,值得探討。
債務愈多和利率愈高,債務的利息負擔就愈重。去年發展中國家支付的利息就達到GDP的1.5%或政府收入的6.9%,佔用了相當的財政空間。在2010至2021年期間,發展中國家的利息增幅就高於醫療或教育開支的增幅。這情況和上文提到的美國相似,但發展中國家不能以自己的貨幣還債,因而債務的可持續性受到相當的約束。
全球債務作為GDP比例的上升,隱含着一個問題,就是債務融資得來的款項,可以促進的生產愈來愈少。按世界銀行的數據計算,1971至2000年期間,全球的年均實質增長率是3.29%,而2000至2022年期間則為2.85%。後22年比前29年公債的發行量明顯更多、增長更快,同時金融市場理應更有效率,但GDP的增長率卻比較慢。大抵政府借來的資金,比較多用在消費性而非投資性的項目,又或用來償還舊債利息而非帶動經濟活動。此外,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美、英、歐、日幾家主要央行的量化寬鬆政策帶來十多年的極低利率環境。資金成本這麼便宜,毋須將資金投放到特別高回報的項目上也有所得,效率也自然下跌。
上文討論的債務、包括總數92萬億美元的都是政府發行的公債。按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報告【註2】,若包括企業和個人債務,全球總債務在今年中達到歷史高峰的307萬億美元,比十年前迅速增加了100萬億美元或50%,增幅驚人。在目前有多方面不明朗的國際政經環境中,這麼多和仍在快速增長的公債和私債,是未來經濟走勢的一大關注點。
【註1】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world-of-debt
【註2】 https://markets.businessinsider.com/news/currencies/global-debt-record-trillion-developed-economies-gdp-us-banks-iif-2023-9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